明清之际,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。在王朝更替,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,许多学者痛定思痛,不约而同地强调崇实黜虚,主张经世致用,努力寻找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方案,尝试开辟新的学术路径和治学方法。他们以深刻的理论思考,犀利的现实批判,求实的学问精神,大胆地阐发个人的见解,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主张,并尽情抒发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深沉的兴亡之感,整个学术界呈现出生动活跃、繁荣兴旺的景象。在此期间,传统史学重新受到学人士子的重视,私家修史热潮迅速发展起来,成为明末清初经世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顾祖禹即是明末清初极具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和历史地理学家,其名著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也备受学人士子推崇。亦因如此,顾祖禹其人、其书引起后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,学界已有不少成果。尤其是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书,成为学界研究热点,学者或考辨其文本流传问题,或考证其文字记载讹谬,或揭示其某一方面的思想内容,尤为强调其军事地理的思想价值。本文意欲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,将顾祖禹置于明清之际王朝更替、社会变化和学术转型的背景之下,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发掘探讨顾祖禹的思想主张,并据此解读分析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成就和特色,以期对全面了解顾祖禹的学术思想与史学成就,更好地把握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变化和转型有所助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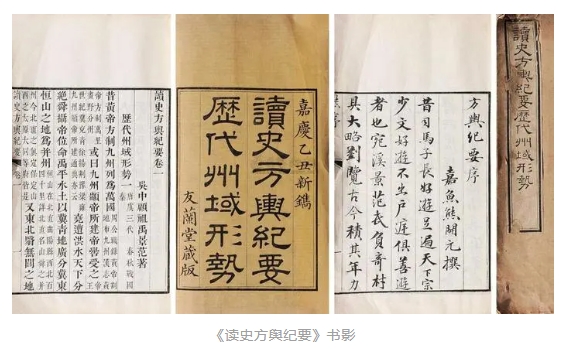
一
顾祖禹,字景范,号宛溪,生于明崇祯四年(1631),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(1692),江苏无锡人,学者尊称为宛溪先生。
顾祖禹先世几代均为明朝官吏。在明代“南倭北虏”,边患未已的情势下,其先人怀抱经世之志,好谈“边徼利病”。至其父亲顾柔谦,生当多事之秋的明季,幼时即遭逢亲死家破的厄运,壮年以后又身历沧桑之变,一生竭蹶窘迫,隐居未仕。坎坷的经历,养成了他淡于名利、崇尚气节的性格,也激励了他奋发读书、勤于思索、以匡时济世为己任的志向。他痛心于当时学者对“封疆形势,惘惘莫知,一旦出而从政,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,曾不若藩篱之限、门庭之阻”的现状,因而精研史地之学,撰有《山居赘论》等书。这些都对顾祖禹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顾祖禹资质聪慧,幼时即能“背诵经史如水”。稍长,博洽群籍,尤“好言地理之学”。明亡后,随父徙居常熟虞山,过着躬耕自食、贫苦困顿的生活。他为人“沉敏有大略”,时刻怀抱兴复之志,与明末遗民范贺、黄庭诸人交游,纵谈古今,议论时事,往往愤懑不能自持。顺治九年(1652)移居无锡胶山后,还经常身着明朝衣冠,往来于胶山之野,以抒发对故国的怀念之情。
顺治十六年(1659),顾祖禹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,开始了考订撰述的工作。由于生活所迫,他不得不担任里中塾师,“岁得脩脯止六金,以半与妇,俾就养父翁家,余尽市纸笔灯油”,用于写作。他无力买书,只有想方设法借钞借读,以资参考。尽管居室“箕帚不具,风雨无所施”,平日“子号于前,妇叹于室”,仍然孜孜矻矻,手不释卷。他广搜博采,“集百代之成言,考诸家之绪论”,即使“单词只字,皆考核再三”,力求“引据不诬,义类可据”。
康熙初年,顾祖禹经过“穷年累月,矻矻不休”的努力,已完成《历代州域形势》初稿。正当他继续撰述南北两京和各省舆地,论次海防海运,考核盐漕屯牧时,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在西南发动了反清战争。顾祖禹得知后,强烈的恢复愿望,竟使他不顾一切,把妻子儿女托付给友人黄庭,只身入闽,参与耿精忠幕中,为其出谋划策,失败后才辗转归家。这次远行,大大丰富了顾祖禹的见闻,他“于舟车所经,亦必览城廓,按山川,稽里道,问关津,以及商旅之子、征戍之夫,或与从容谈论,考核异同”,获取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,为他进一步考核撰述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《大清一统志》开馆,总裁徐乾学素知“祖禹精地理学,固延之。三聘乃往”,先到京师,后又至洞庭包山。在志局中,顾祖禹与当时著名学者阎若璩、黄仪、胡渭诸人共同研讨,相互交流,又得饱览天下舆地图册及徐氏传是楼藏书,大大增长了学识,开阔了视野。《大清一统志》书成之后,徐乾学欲列顾祖禹之名呈上朝廷,但他坚辞不允,“至欲投死阶石,始已”,反映了他砥砺气节、耻于名利的态度。
离开志局,顾祖禹又复归里,仍继续进行考订撰述的工作,直至去世。经过前后长达三十余年的不懈努力,顾祖禹终于撰成一部贯穿古今、网罗一代的历史地理学巨著——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。
二
在亲身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之后,顾祖禹和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,致力于思考“四海陆沉,宗社丘墟”的原因。与此同时,家庭的熏陶,父亲的影响,又使得他的学术思想主张在与同时代有识之士的共鸣之外,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。
1.强烈的经世之志
目睹明末空疏学风造成的危害,明清之际的学人士子不约而同地倡导实学,强调经世致用。颜元明确指出,“救弊之道,在实学,不在空言”,若“实学不明,言虽精,书虽备,于世何功,于道何补!”李颙大力倡导“道不虚谈,学贵实效”,揭橥“明体适用”之学,认为“吾儒之教,原以经世为宗”,主张“吾辈须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。穷则阐往圣之绝诣,以正人心;达则开万世之太平,以泽斯世。”陆士仪认为:“今人所当学者,正不止六艺,如天文、地理、河渠、兵法之类,皆切于用世,不可不讲。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,徒高谈性命,无补于世,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”。朱之瑜也明确主张:“为学当有实功,有实用。”强调“巨儒鸿士者,经邦弘化,康济艰难者也。”黄宗羲更以东南儒宗的气魄,豪迈地宣称:“儒者之学,经纬天地。”倡导“经术所以经世”,主张学者应当以天下为己任,究心实务,建立功业,达到“学道”与“事功”二者的统一。顾炎武则明确提出,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“明道”“救世”,读书撰文都应当有益于天下,有裨于世务,真正做到“拯斯人于涂炭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与众多思想家学者发出的崇实黜虚、经世致用的呼声相比,顾祖禹的经世主张,带有鲜明的重视舆地的特色。他认为:“凡有志于用世者,河渠、边防、食货、兵制,皆其所有事也。然而莫重于舆图。”这是因为舆地之学是关系建国经邦、经济民生的重要学问,举凡“战争攻守、废兴成败、利钝得失之迹,以迄耕屯盐铁、经国阜民诸大政,有一不本之方舆者耶!”无论从历史来看,抑或就现实而言,舆地之学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,所谓“天子内抚万国,外莅四夷,枝干强弱之分,边腹重轻之势,不可以不知也。宰相佐天子以经邦,凡边方利病之处,兵戎措置之宜,皆不可以不知也。百司庶府,为天子综理民物,则财赋之所出,军国之所资,皆不可以不知也。监司守令,受天子民社之寄,则疆域之盘错,山泽之薮慝,与夫耕桑水泉之利,民情风俗之理,皆不可以不知也。四民行役往来,凡水陆之所经,险夷趋避之实,皆不可以不知也”。据此,顾祖禹明确指出:“学者且毋言博稽群籍也,于方舆一书,能审厥源流,推之经史实学,思过半矣。”然而,尽管舆地之学关系如此重大,明代学者却大多“尊耳贱目,忽近骛远”,崇尚言心言性,“谈及方舆,辄谓非所亟也”,致使《大明一统志》那样重要的舆地著作,也“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,类皆不详,于山川条列,又复割裂失伦,源流不备”,这不能不说是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因此说,顾祖禹着眼于舆地之学的经世主张,既是他发愤撰写方舆著作的根本动力,也与当时有识之士的经世呼声相辅相成,促进了明清之际学术风气的转换。

2.深沉的兴亡之感
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,代明而兴的既是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王朝,又是一个依靠军事征服战争和政治高压手段建立的统治政权。这种严酷的现实,对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熏陶,坚持华夏正统观念的汉族知识分子而言,不啻是一场“神州荡覆,宗社丘墟”的巨大灾难。因此,许多汉族士子在武装反抗失败,复明无望之后,仍拒不与清统治者合作,他们或遁迹山林,或隐居著述,把满腔悲愤,寄托在语言文字之中,顾祖禹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早在南宋时期,其家族先人顾原九即于理宗端平元年(1234) “由临安避地梁谿,耕读于宛谿之上,子孙奉遗命,历元世皆隐居不仕”。其父顾柔谦身历明清易代,同样隐遁山中,躬耕自食。顾祖禹绍继家风,亦以明代遗民自任,时刻怀抱兴复之志,为参与抗清斗争,甚至不惜身家性命。尽管恢复无望,生活又穷困竭蹶,他仍然坚持不食清廷俸禄,不受清廷恩惠,始终保持了高尚的节操。并且,顾祖禹还把他的思想、情感、志向乃至愤懑、无奈,托之于文字著述。姑且不论其巨著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即便是在他残存的诗文著述中,这种强烈的兴复之志、故国之思和兴亡之感,也随处可见。如他为当时学人孙治《孙宇台集》作序,称其“先识远略,蚤知覆压之不免,思欲以身拯其弊,谓俗学嚣浮,不足措诸实用,其于兵刑、财赋、农桑、水利诸书,罔不穷源悉委,思一见诸行事。乃沧桑屡变,陵谷俱倾,故旧知交,死亡契阔,而先生抵掌挥毫之风,概尽摧残于悲禾泣黍中,不复有当年逸事矣”。又谓其“博学多闻,自经史以迄诸子百家、昭代典故,无不谙练,上下古今,论列人材,指陈得失,皆精当不可易。其为文不名一家,而尤喜龙门,意所欲言,则奋笔出之,晚年益进于高洁。其于诗出入骚、雅,揖让三唐,非近今凡响也。然而先生故不乐以诗文自表见矣。其于世道民生、人情风俗之故,每有感触,则终夜踌躇,当食长叹曰:不意当吾之世,乃凌迟以至于此!”其间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感,与其说写的是他人,毋宁说是顾祖禹自身经历的真实写照。诚如黄宗羲所言:“嗟乎!亡国之戚,何代无之?使过宗周而不悯《黍离》,陟北山而不忧父母,感阴雨而不念故夫,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,是无人心矣!故遗民者,天地之元气也……自有宇宙,只此忠义之心,维持不坠。”可以说,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,包括顾祖禹在内的诸多学人士子所表现的民族气节,所高扬的民族意识,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,也成为当时实学思潮和经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3.自觉的传承意识
鉴于明末以来学术界“束书不观,游谈无根”的空疏学风,学人士子普遍重视读书,倡导实学。黄宗羲批评“明人讲学,袭语录之糟粕,不以六经为根柢,束书而从事于游谈,故受业者必先穷经,经术所以经世”,认为“读书不多,无以证斯理之变化”。顾炎武提倡“博学于文”,强调“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,皆学之事也”,主张“博学审问,古人与稽,以求其是非之所在”。顾祖禹则秉承家学,发愤接续其家族“自两汉以来,称为吴中文献”的传统。他梳理顾氏家族的历史渊源,特别提到三国时期的吴国重臣顾雍,称其“以功名显,累传以降,皆有功德文章,载在史册”;南朝时期的顾野王,则“以著述显于梁、陈之际,所著书数百卷,而《舆地志》尤见重于世,至今学者犹宗师而俎豆之”。至明成化年间,顾允敬始官于朝;嘉靖中,顾大栋“好谈边徼利病,跃马游塞上”,“撰次《九边图说》,梓行于世”;万历时,顾文耀“奉使九边,还对,条奏甚悉,天子称善”。其父自幼即好读书,“补邑弟子员,深慨科举之学不足裨益当世,慨然欲举一朝之典故,讨论成书”。然天不遂人愿,遭逢明清易代,躬耕田野,赍志而没。临终前留下遗命:“吾家自两汉以来,称为吴中文献,先代所著述,小子可考而知也。士君子遭时不幸,无可表见于世,亦惟有掇拾遗言,网罗旧典,发舒志意,昭示来兹耳。尝怪我明《一统志》,先达推为善本,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,类皆不详,于山川条列,又复割裂失伦,源流不备。夫以一代之全力,聚诸名臣为之讨论,而所存仅仅若此,何怪今之学者,语以封疆形势,惘惘莫知,一旦出而从政,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,曾不若藩篱之限、门庭之阻哉!先光禄在世庙时,傍徨京邑,岌岌乎有肩背之虑,图论九边,以风示谋国者。先奉训当神庙中,四方无虞,以边备渐弛,伏戎可虑,先事而忧,卒中忌讳,仕不获振。先文学请缨有志,揽辔无年。及余之身,而四海陆沉,九州腾沸,仅获保首领,具衣冠,以从祖父于地下耳。嗟乎!园陵宫阙,城郭山河,俨然在望,而十五国之幅员,三百年之图籍,泯焉沦没,文献莫征,能无悼叹乎!余死,汝其志之矣!”可以说,家族的传统,先世的功业,尤其是父亲的耳提面命,对顾祖禹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他以保存图籍、传承文献、撰述著作为己任,“思欲远追《禹贡》《职方》之纪,近考《春秋》历代之文,旁及裨官野乘之说,参订百家之志,续成昭代之书,垂之后世,俾览者有所考镜”。正是在这种自觉的文献传承信念支撑之下,顾祖禹不惜穷毕生精力,撰成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书,成就了名山事业。
4.卓越的史地观念
明末清初,随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实学思潮的兴起,史学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。当时有“一代文宗”之称的钱谦益,曾高度评价史学的价值:“史者,天地之渊府,运数之勾股,君臣之元龟,内外之疆索,道理之窟宅,智谞之伏藏,人才之薮泽,文章之苑圃。”认为读史能使人“耳目登皇,心胸开拓,顽者使矜,弱者使勇,怯者使通,愚者使慧,寡者使博,需者使决,憍者使沈”。黄宗羲也极为重视史学,认为“二十一史所载,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”,主张“学必原本于经术,而后不为蹈虚;必证明于史籍,而后足以应务,元元本本,可据可依。”王夫之明确指出:“所贵乎史者,述往以为来者师也。为史者,记载徒繁,而经世之大略不著,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,则恶用史为?”顾炎武强调史学的“资治”功能,认为“史书之作,鉴往所以训今”,学者若能于历史上的“进取之得失,守御之当否,筹策之疏密,区处兵民之方,形势成败之迹,俾加讨究,有补国家”。
顾祖禹既受到当时学界风气变化的影响,又深受家学的熏陶,重视史学,尤重舆地。他批评宋元以来学人士子轻视史学、不讲舆地的弊端,谓“近时史学益荒,方舆一家尤非所属意”,强调“不考古今,无以见因革之变;不综源委,无以识形势之全。”又明确指出;“读史有四难:方舆之迷缪,一也;年号之错杂,二也;谱系之淆乱,三也;职官之纷更,四也。”乾嘉时期史学大家钱大昕曾说,“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:曰舆地,曰官制,曰氏族”,可谓与顾祖禹所见略同。顾祖禹还十分重视舆图,他说:“风后受图,九州始布,此舆图之始也;《山海》有经,为篇十三,此地志之始也。《周礼》大司徒而下,职方、司书、司险之官,俱以地图周知险阻,辨正名物。战国时苏秦、甘茂之徒,皆据图而言天下险易。萧何入关,先收图籍,邓禹、马援,亦以此事光武,成功名。儒者自郑玄、孔安国而下,皆得见图籍,验周、汉山川。盖图以察其象,书以昭其数,左图右书,真学者事也。”这些见解,都反映了顾祖禹的卓识。尤为难得的是,顾祖禹对历史与地理的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知,强调二者密不可分,认为“史其方舆之向导”,“方舆其史之图籍”。他说:“古来作史者必本诸方舆。太史公书夐绝千古,而得之游历者居多。后之作者,或未能通其义,史学所以日衰也。夫作史者不可不知方舆,读史者又可不知方舆耶!近来言史之家不必致详于方舆,方舆诸书又未尝博征之史,余窃病焉。”鉴于前代学者大多“以史为史,而不能按之于舆图;以舆图为舆图,而不能稽之于史”的弊端,顾祖禹在自己的研究中,自觉地把史、地二者联系起来,“出入二十一史,纵横千八百国”,“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,即以古今之史,质之于方舆”,“凡形势之险阨,道里之近遥,山水之源委,称名之舛错,正其讹,核其实,芟其蔓,振其纲”,撰成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百三十卷,附《舆图要览》四卷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说:“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。”今人认为:“历史决定思维的深度,地理决定视野的广度,理清地理问题,才能理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根源、走向与结果,而这也是解读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。”由此观之,顾祖禹对史地关系的深刻揭示及其成功的学术实践,无疑反映了他思想的深度和视野的广度,无论是在当时抑或今日,都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。
三
在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荡涤下,学界一反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史学,排斥事功的倾向,转而崇尚史学,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价值,掀起了私家修史的热潮。许多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家国之痛的学者,怀抱强烈的民族意识,着眼于经世致用的目的,致力于当代史的纂修,尝试各种体裁史著的撰写。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就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著述之一。
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凡一百三十卷,附《舆图要览》四卷。全书以明代建置区划作为编排纲目,前九卷论次历代州域形势,中一百十四卷分述南北两京及各省舆地,末七卷详载川渎源委异同及天文分野。顾祖禹的用意在于:“首以列代州域形势,先考镜也。次之以北直、南直,尊王畿也。次以山东、山西,为京室之夹辅也;次以河南、陕西,重形胜也;次之以四川、湖广,急上游也;次以江西、浙江,东南财赋所聚也;次以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,自北而南,声教所为远暨也。又次以川渎异同,昭九州之脉络也。终之以分野,庶几俯察仰观之义。”全书不仅编排谨严有序,在叙述方法上也颇为精当。论次历代州域,以朝代为经,舆地为纬,使读者开卷即对“州域之分合,形势之重轻了然于中”。叙述两京及各省形势,则以舆地为经,朝代为纬,每省卷首皆冠以总序一篇,论述各省疆域形势、地理沿革及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道,然后列举省下所辖各府县以及全省境内主要山川、桥梁、关隘。其下分述各府以及所辖各县亦仿此例,而叙述更为详密。所附《舆图要览》四卷,则首列《舆地总图》,次列南北两京及各省舆图,其后专列《九边总图》,末列黄河、海运漕运等图。各图所涉地域区划,以及道里远近、山川形势等,均有详尽的说明文字,与全书正文所述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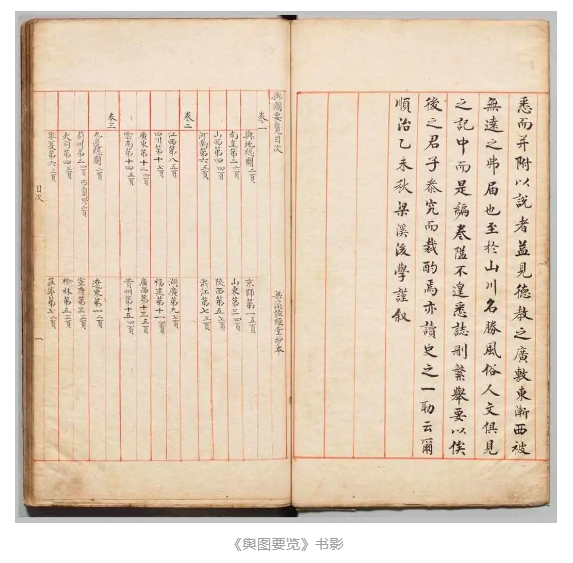
在明末清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,顾祖禹把他的思想主张贯穿于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撰写中,由此而形成了是书的鲜明特色。
1.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
以往的舆地志书,内容大多偏重于名胜古迹及词人骚客的游览赋诗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 则不然,它详于疆域形势、山川险要,每叙一省一府、一县一地,无不备载“疆域、名山、大川、重险,俾一方之形势,灿列在前”。特别对历史上有关“大经大猷,创守之规,再造之绩,孰合孰分,谁强谁弱,帝王卿相之谟谋,奸雄权术之拟议,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”,叙述尤为详明,而对景物游览之胜则多所从略。以直隶为例。顾祖禹于首卷即直陈其疆域形势,谓其“雄峙东北,关山险阻,所以隔阂奚戎,藩屏中夏。说者曰:沧海环其东,太行拥其右,漳卫襟带于南,居庸锁钥于北,幽燕形胜,实甲天下”。进而从全国的范围来看,“秦晋为之唇齿,而斥堠无惊;江淮贡其囷输,而资储有备。鱼盐枣栗,多于瀛海碣石之间;突骑折冲,近在上谷、渔阳之境。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,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,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规也。”但直隶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弱点,所谓“居庸当陵寝之旁,古北在肘腋之下。渝关一线,为辽海之噤喉;紫荆片垒,系燕云之保障。近在百里之间,远不过二三百里之外。藩篱疏薄,肩背单寒。老成谋国者,早已切切忧之。”顾祖禹不仅对直隶形势要害了如指掌,还对此地历史上的兴亡成败之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。他在备述先秦至明历代战守攻取事宜之后,对明末的直隶及全国局势作了精辟的分析,认为当时已是“关塞之防,日不暇给,卒旅奔命,挽输悬远。脱外滋肩背之忧,内启门庭之寇。左支右吾,仓皇四顾,下尺一之符,征兵于四方,恐救未至,而国先亡也。撤关门之戍,以为内援之师,又恐军未离,而险先失也。甚且藉虎以驱狼,不知虎之且纵其搏噬;以乌喙攻毒,而不知乌喙之即足以杀身也。不亦悲哉”!字里行间,既反映了顾祖禹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,也流露出他对亡明的深切痛惜之情。
对明代的边防情势,顾祖禹尤为关注,他说:“明初边备,自辽东而大宁,而开平,而宣府,而东胜,而大同,而宁夏,而甘肃,东西延亘,指臂相依,称全盛焉。”明中叶以后,“大宁既失,开平、兴和又弃,东胜复捐,于是残缺之形日以滋长。也先、火筛而后,戎狄益起骄心,吉囊尤称雄桀,跳梁之祸,无日而间,边境诸方,骚然不宁矣。逮乎末季,法令日玩,敝坏日生,匮乏日甚,补救犹曰不遑,孰敢撄其锋而与之抗哉?”因此,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书中,对明代九边地区,尤其是辽东重镇所在各地的山川形势、道里远近、风俗民情、建置沿革等作了翔实的记述。如原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属自在州清河堡一地,顾祖禹记载说:“司东南三百里。南临太子河堡,西有白塔佃,可按伏。又西有威宁营,可屯兵。其东接鸦鹘关往来。志云:清河堡东境有松山,军士采木处也。《舆程记》:出清河路三十里即鸦鹘关,又三十里至响花岭,五里为撒石寨,十里无狼寨,十里旧鸦鹘关,十里一哈河,十五里乌鸡关,二十里林子岭,二十里错罗必寨,又三十里即建州老寨矣。其旧鸦鹘路坦无林,四马可进;乌鸡关头道扣栅有悬崖相抱,二道砌石横木,止容一人俯行,骑不能过;林子岭树虽稠密,亦四马可行也。”此段文字自“志云”以下一段有关建州老寨的记载,因涉及满族先世发祥之地,在顾祖禹身后是书的流传过程中,抄写者恐涉忌讳,将其全部删除。直至今日,学者点校整理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将后世流传抄本及通行刻本与顾祖禹原稿本相核对,才发现其中被删除的文字竟达四十条之多。
由此可见,在清初统治尚未完全巩固,全国抗清斗争尚未完全平息的情势下,顾祖禹偏重军事地理,详载明代九边情势,其经世致用的旨意是颇为深长的。无怪当时同抱遗民之感的魏禧等学者,评论此书“贯穿诸史,出以己所独见,其深思远识有在于语言文字之外,非方舆可得纪者”。后世学者甚至直接将其视之为军事著述或军事地理之作,如张之洞即将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归入兵家类,谓“此书专为兵事而作,意不在地理考证”;梁启超说:“景范这书,专论山川险隘,攻守形势,而据史迹以推论得失成败之故。其性质盖偏于军事地理,殆遗老力谋匡复所将有事耶?”这些看法,确实反映了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书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。
2.深切的人文关怀
军事地理而外,顾祖禹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地理也十分重视。他认为方舆志书的内容,应当包括河渠、食货、屯田、马政、盐铁、职贡等项在内,“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”。因此,他在叙述各省区疆域形势的同时,往往能简明扼要地点出当地的经济优势和农业生产的特点。如论江南形势及经济物产状况:“以东南之形势,而能与天下相权衡者,南直而已……江淮之间,五方之所聚也,百货之所集也,田畴沃衍之利,山川薮泽之富,远近不能及也。”对其故里无锡所在的常州府,顾祖禹也准确地揭示出其地利物产及形胜特色:“府北控长江,东连海道,川泽沃衍,物产阜繁,周处所云三江之雄润,五湖之腴表也。且地居数郡之中,翼带金陵,为转输重地,脱有不虞,则京口之肘腋疏,而吴郡之咽喉绝。若其北守靖江,则内可以固沿海之锁钥,外足以摧淮南之藩蔽;南扼宜兴,则近足以消滨湖之窥伺,远可以清浙右之烽烟。昔者南唐守此,以御吴越,明初得此,以制姑苏郡,岂非东南之襟要欤?”
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江河湖海的源流、变迁及利弊形势,顾祖禹除在各省区分别叙述外,还专辟“川渎”一编,对黄河、长江、淮水、汉水、盘江等重要江河,穷原竟委地加以叙述。而且,不仅从自然地理的角度,叙其发源、流变,还着重从经济地理的角度,述其灾害和治理。如黄河,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源地,它哺育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,也给沿岸人民带来过巨大的灾难。顾祖禹用两卷的篇幅,详考其发源、河水流向及河道变迁,历述其在历史上造成的巨大灾害,指出“河之患,萌于周季,而浸淫于汉,横溃于宋。自宋以来,淮、济南北数千里间,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”。“至于晚近,且谓御河如御敌,庙堂无百年之算,闾阎有旦夕之忧”,“国计民生,靡所止定矣”。出于对河患灾害的巨大忧虑和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,顾祖禹辑录了汉代以来诸多有识之士,如汉贾让,北魏郑偕,宋欧阳修、苏辙、任伯雨,元欧阳玄,明徐有贞、潘季驯等人提出的治河主张,尤其赞同潘季驯提出的“以堤束水,借水攻沙”这一有效的“以水治水之良法”。而对统治者上层或言“别穿漕渠,无藉于河”,或谓“弃地以畀河,使遂其游荡”等但求漕运通畅,不顾民众安危的观点,则给予了严厉的斥责。提出治河之根本在于“人事修举”,或疏或浚,或堤或塞,“要以与时变通,因端顺应,本之以己溺己饥之心,揆之于行所无事之智,河未必终于不可治也夫!”这些叙述和议论,都鲜明地体现了顾祖禹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和鲜明的经世致用思想。
3.可贵的辩证思想
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书中,顾祖禹偏重军事地理,详载各地山川形势,纵论攻守战取之道,因而他十分看重“地利”的作用,认为“地利之于兵,如养生者必藉于饮食,远行者必资于舟车也”。但顾祖禹并非地理决定论者,他虽然重视地理形势,但并不认为地理条件是绝对的,关键还在于人去掌握利用。由此出发,他在对地理形势和古今战守攻取事宜的叙述中,强调人的因素,表现出了可贵的辩证思想。他说:“地利亦何常之有哉!函关、剑阁,天下之险也。秦人用函关,却六国而有余;迨其末也,拒群盗而不足。诸葛武侯出剑阁,震秦陇,规三辅;刘禅有剑阁,而成都不能保也。故金城汤池,不得其人以守之,曾不及培塿之丘、泛滥之水;得其人,即枯木朽株,皆可以为敌难。是故九折之阪,羊肠之径,不在邛崃之道,太行之山;无景之溪,千寻之壑,不在岷江之峡,洞庭之津。及肩之墙,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;渐车之浍,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。”因而“起于西北者,可以并东南;而起于东南者,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。故曰:不变之体,而为至变之用;一定之形,而为无定之准。阴阳无常位,寒暑无常时,险易无常处。知此义者,而后可与论方舆”。在考论历代州域形势时,顾祖禹也明确指出:“州域之建置有定,而形势之变动无方。譬之奕焉,州域其画方之道也,形势其布子之法也。譬之治田者焉,州域其疆理之迹也,形势其垦辟之宜也。布子同而胜负不同,则存乎奕者之心手而已矣。垦辟同而获否不同,则存乎田者之材力而已矣。”魏禧在读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书后,特别指出“其论之最伟且笃者”有二:“一以为天下之形势视乎建都,故边与腹无定所,有在此为要害而彼为散地,此为散地而彼为要害者;一以为有根本之地,有起事之地,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,而起事者不择地。”诸如此类,这些深得时人推崇的精辟见解,实际上正是顾祖禹难能可贵的辩证思想的反映。
明末清初,在王朝更替的社会大变动情势下和学术转换的思想潮流中,顾祖禹以其卓有识见的经世思想和史学主张,为实学思潮的发展和经世史学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。尤其是其倾尽毕生心血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一书,得到了当时及后世学者的高度赞扬。时人将其与梅文鼎《历算全书》、李清《南北史合注》相提并论,誉之为“三大奇书”。孙治“尝读其书,谓如长河亘天,珠囊照地,古今兴亡,天下形势,瞭如指掌,人间所未有也”。魏禧慨叹说:“有是哉!此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也。”吴兴祚认为:“其词简,其事核,其文著,其旨长,藏之约而用之博,鉴远洞微,忧深虑广,诚古今之龟鉴,治平之药石也。有志于用世者,皆不可以无此篇。”江藩也推崇说:“读其书,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。为地理之学者,莫之或先焉。世所称三大奇书,此其一也。其二则梅文鼎《历算全书》、李清《南北史合钞》。然合钞本人所易为,李书尤嫌疏漏,岂能与顾氏、梅氏之书鼎足哉!”这些评价,对顾祖禹而言,是当之无愧的。
(作者单位: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)









